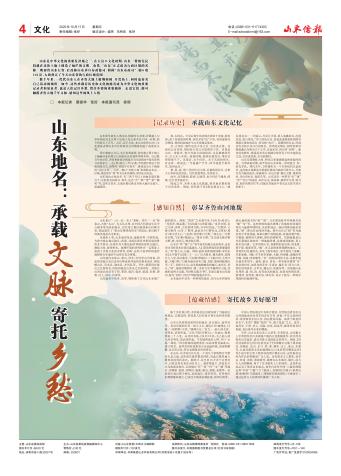□本报记者 蔡振华 张好 本报通讯员 徐丽
山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一带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金代,“山东”正式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明初置山东行省,后改称山东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山东布政司”,辖6府104县,大致奠定了今天山东省的行政区域范围。数千年来,一代代山东人在齐鲁大地上披荆斩棘、开荒拓士,同时也命名自己活动的场所。如今,这些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地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记录者和见证者,也是人们记住乡愁、留住乡情的重要载体。走近它们,便可触摸齐鲁大地千年文脉,感知这里的风士人情。
【记录历史】承载山东文化记忆
山东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根据考古发现,沂源猿人与举世闻名的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基本处于同一时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之后,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表明山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创造了高度的文明。
周王朝建立之后,实行封邦建国,把为建立周王朝立下赫赫功业的周公旦和姜尚分封到鲁国和齐国。经过数百年的经营,齐国和鲁国分别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使臣韩宣子到鲁国观书后,曾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成为天下倾慕的“礼仪之邦”。后世一般以“齐鲁大地”来指称山东这一区域,现在更以“鲁”作为山东的简称,原因正是在此。
山东境内古国众多,有三四千年以上的地名就有数百个,比较著名的除齐、鲁外,还有“莒”“郯”“费”“莱”“颛臾”等,这些古国名、古地名都反映出齐鲁大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郯,古国名。少昊后裔中的炎族首领封于炎地,称炎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名多加“邑”字旁,炎国遂演变为郯国,郯国的故地在今山东郯城县境内。
莒,古国名,相传也是少昊之后,为东夷古国。在商代已有莒国,周初封少昊之后兹舆其于莒。莒国是山东一带除齐、鲁之外最大的诸侯国,先是被楚国所灭,后又并入齐国。战国时期,燕国乐毅伐齐,唯有莒和即墨不下。汉置县,至今仍存。关于莒国的得名,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地盛产芋艿,因当地把芋称作莒,故得此名。”
费,夏、商、周三代时均为小国,后被鲁国吞并,为鲁大夫季孙氏的封邑。汉代始置费县,沿用至今。此外,还有滕国、薛国、纪国等,如今仍存于滕州、薛城、纪台村等地名中。
除此之外,齐鲁大地文化繁盛,很多地名都来源于历史事件。例如,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云:“城在莱芜谷……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人流播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济宁的鱼台县,传说此地曾建鲁国国君鲁隐公观鱼的高台,所以称“鱼台”。淄博的桓台县,因境
内有齐桓公戏马台而得名。菏泽的定陶区,相传春秋时期范蠡认为陶为天下之中,在此定居,所以叫“定陶”。曲阜的驻跸村,据说是宋真宗到曲阜祭拜孔子时中途休息之处,后形成村落,名为驻跸村。
山东东部濒临大海,明代以来屡遭倭寇和海盗的侵扰。自明成祖时期,就开始在山东沿海一带设置卫、所,驻扎军队。明代末年,卫所制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日益废弃,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普通村落或当地的行政中心,并演变为当地的地名,如威海市、灵山卫镇、鳌山卫镇、雄崖所村、浮山所社区、海阳市等。山东还有一些带有“屯”“寨”“营”“官庄”的地名,如丰乐屯、韩家寨、德州甲马营、哨马营、临沂的蔡官庄等,仍能从其地名中看出过去驻军戍守的影子。
【感知自然】彰显齐鲁山河地貌
山东素以“一山一水一圣人”著称。其中,“一山”指泰山,古称“太山”,为五岳之尊,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据非常崇高的地位,历代帝王都以能到泰山封禅为荣,因此就有了“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说法,泰山脚下的城市遂命名为泰安。
从地形上看,山东地形复杂,地貌多样,中部突起,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西部、北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东部半岛大都是起伏和缓的波状丘陵区,濒临大海,海湾密布。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齐鲁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这些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特点在地名中也得以充分体现。
山东境内有泰山、蒙山、济水、沂河等山川河流,因此很多地方是以这些山峰或者河流的名称来命名,例如崂山区、沂水县、泗水县、齐河县等。另外,蒙阴因在蒙山之北而得名,济阳因地处古济水之北而得名。其他以山河命名的还有宁阳、莱阳、临沂、临沭、临淄、沂源、即墨、汶上、河东、沂南等。山东地名中的泽、泊等,则体现了古代山东水域广阔的特点。例如,“菏泽”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导菏泽,被孟潴。”《风俗通•山泽篇》载:“水草交厝,名之为泽;泽者,言其润泽万物,以阜民用也。”巨野泽,又称大野泽、大泽、广野泽,故址在今巨野县北。《周礼•夏官•职方氏》云:“(兖州)其泽薮曰大野。”郑玄注:“大野在巨野。”《尔雅•释地》云:“鲁有大野。”汉以前文献多称大野;唐、宋以后,则多称巨野。
山东以“阜”“陵”“丘”等字命名的地方也有很多,这是因为当时洪水经常泛滥成灾,人们喜欢择高而居来躲避洪灾。“阜”指土山、丘陵。例如,曲阜是鲁国的国都,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一云:“汉为鲁县,魏为曲阜,委曲长七八里,故曰曲阜。”《尔雅•释地》云:“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以陵为地名的有兰陵、乐陵、德州的陵城区等。“丘”,多指小土山,也可指地势略高的地区,如安丘、章丘。“阿”,战国时期因济、濮二水沿今东平湖两岸入境,河曲形成两大丘陵,当时称丘陵为“阿”,东面丘陵在山东境内,称为“东阿”,因出产阿胶而驰名中外。
山东地名中还有一些特殊的通名,如与山东西部沂蒙山地形相关的“峪”“崮”,与东部的海洋环境相关的“疃”“夼”等。这些特殊的通名体现了该地特有的地形特点与地理环境特征,从而形成这一地区特殊的地名景观。“峪”,即山谷山间的谷地。鲁中山区以“峪”作为地名用字非常普遍,如泰山脚下的桃花峪,济南的葫芦峪、万粮峪,蒙阴的大寨峪,潍坊的蒋峪等。岱崮地貌是山东沂蒙地区独有的一种地貌景观,是指四面陡峭、顶上较平的山体。它多用作山名,如蒙阴的孟良崮、卧龙崮、獐子崮、板崮崖等。“疃”,本义是指禽兽践踏的地方。它常用作村名通用名,多见于胶东地区,如平度的兰家疃、东崔家疃、马疃,牟平的李家疃、大疃、西留疃,诸城的常吉疃、东疃、时家疃等。“夼”,指两山间的大沟,是胶东地区地名常用字。威海、烟台、青岛一带有很多使用“夼”命名的村庄,如青岛的草夼、车家夼、拖车夼、西九六夼,烟台的刘家夼、正甲夼、藏金夼、泥渡夼等。沿海地区还有用湾、港、咀、泊、岛等命名的地名,如青岛的唐岛湾、胶州湾、鱼鸣咀、蜊叉泊、团岛等,显示了胶东一带海岸线曲折的地理环境。
【蕴藏情感】寄托故乡美好愿望
除了历史和自然,有些地名还直观反映了当地的宗族观念、宗教信仰,寄托着人们对家乡和生活的美好愿望。
山东以民间传说而得名的地名,有女姑山、嘉祥县等。青岛市城阳区有一座小土丘,据《汉书•地理志上》载:“(琅邪郡)不其。”颜师古注:“有太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元代于钦《齐乘》云:“女姑山,即墨西南三十八里。山北旧有基,《汉书》不其:太乙仙人祠九所及明堂,皆武帝所起。不其城西南有七神,号曰‘女姑’,即此。”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汉武帝曾登临此山,建立明堂。嘉祥县因传说鲁哀公在此地狩猎,获瑞兽麒麟,是吉祥之兆,所以金朝置县时而得名。在山东,许多村庄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家族数百年繁衍生息之地,这些成员通常都是同姓,因此以聚居地人数较多的姓氏命名。据统计,在全省10万多个自然村中,以姓氏得名者在60%以上。通常情况下,其命名方式为前面是姓氏,后面缀以“庄”“家”“村”“屯”“楼”等通名,如阚家、倪村、刘埠村、杨集、喻屯、赵楼、孟楼等。有的村庄冠以两个姓氏,如刘孟庄、张李村等。有些村庄的规模越来越大,已成为乡镇或县城驻地,如李庄镇等。
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有择吉情结,历代统治者在给自己的辖地命名时多采用含有吉祥、祈福、平安之意的词语,希望政权长治久安、国运繁荣昌盛。如济宁寓意济水安宁,东营广饶取“海滨广斥,饶于鱼盐”之义。此外,如昌乐、宁津、庆云、乐陵、沾化、招远等,都寄托着美好祝愿,表达着对未来的期盼。
另外,自古以来山东人文荟萃、学者辈出,山东籍文人学者创作出许多家喻户晓的文化典籍著作,其中涉及很多山东地名,成为齐鲁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例如,《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孟子》等典籍中记载了很多地名,如陬邑、尼山、长勺、费、郯、颛臾、汶上、泰山、东蒙等,已成为儒家文化的地理标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活动范围大都在山东,这些地名也因为作品的传播而广为人知。还有很多文人墨客,如李白、杜甫、苏轼、郑板桥等,都曾在山东游历、做官,或与友人诗酒酬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作品也记录了很多山东地名,如李白诗作中的“兰陵美酒郁金香”中的“兰陵”(今兰陵县),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密州(今诸城市),郑板桥任职的潍县(今潍坊市),通过这些文人故事的传播而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