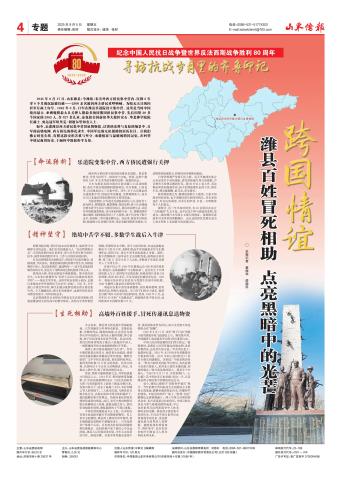□ 本报记者 蔡振华 侯晓民
1945年8月17日,山东潍县(今潍坊)东关外西方侨民集中营内,压抑3年零8个月的沉寂被打破——2300余名被囚西方侨民欢呼呐喊,为暗无天日的囚居岁月画上句号。1942年3月,日军在潍县乐道院设立集中营。这里是当时中国境内最大、亚洲规模最大且关押人数最多的同盟国侨民集中营,先后囚禁20多个国家的2382人,含327名儿童,还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恒安石、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奥运冠军埃里克·利迪尔等知名人士。
如今,走进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泛黄的史料与复原的场景中,日军的高墙电网、西方侨民的挣扎求生、中国军民的无私援助仍历历在目。让我们拂去时光尘埃,打捞这段交织苦难与坚守、承载情谊与温暖的跨国记忆,在回望中铭记血泪历史,于缅怀中汲取和平力量。
【命运转折】 乐道院变集中营,西方侨民遭强行关押
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的前身潍县乐道院,曾是集教堂、学堂与诊所于一体的安宁之地。然而,这种宁静却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日本为报复美国对国内日裔美籍人士活动的限制,竟在中国全境搜捕同盟国侨民,并在香港、上海龙华、山东潍县设立三大集中营。其中,位于山东潍县的乐道院集中营,因地处华北腹地、关押规模庞大,成为长江以北地区同盟国侨民的主要囚禁地。
为强化管控,日军赶走乐道院的原住人员,强征劳工砍光树木、拆毁建筑、修筑碉堡、架设电网,将160亩场地分割为看守生活区与侨民居住区。侨民的囚禁生活,从居住环境便透着颓丧。床与床的间距不足一尺,简陋的烘炉难以御寒,两间淋浴房供上千人使用。孩子们为省下鞋子过冬,春夏秋三季只能赤脚行走。在这里,粮食实行配给制,数量极少且多腐烂变质,药品奇缺问题更为致命,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将侨民的苦难推向极致。
日常管控则严苛到不近人情。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是雷打不动的规矩,侨民需按编号用日语报数,声音稍有不对便会遭到打骂。除80岁以上老人外,其余都必须参加强制劳动,孩子们课前课后也得干活,稍有不从,便会被脚踢、扇耳光,甚至暴打。
除肉体折磨之外,精神的煎熬令人绝望。大家不知战争何时结束,也不清楚囚禁生涯何时到头。对未来的迷茫、对自由的渴望、对亲友的牵挂,日复一日啃噬着每个人的意志。
据统计,近三年半的时间里,有40名侨民在这片“人间地狱”失去生命。这不仅是个体与家庭的悲剧,更成为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铁证,深刻烙印着战争对无辜者的残酷碾压,也让这段侨民受难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无法磨灭的沉痛记忆。
【精神坚守】 绝境中苦学不辍,多数学生战后入牛津
即便身陷囚笼,侨民们也未向苦难低头,始终坚守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自发组建起九人“自治管理委员会”,不仅统筹侨民的日常事务,更与日军看守展开谈判、抗争,最终争取到组织学习、工作与文体活动的权利。
在自治管理委员会的推动下,侨民们可以组织舞会、戏剧表演、节庆活动。热爱绘画的侨民将集中营生活、园内植物绘于纸上,作品色彩绚烂、通透明亮——这不仅是他们排解苦闷的方式,更是为了用鲜活的色彩抚慰孩子的心灵。
教育的火种,更是在困境中顽强燃烧。集中营内的学生,大多来自曾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语学校”——烟台芝罘学校。这所学校由传教士创办,长期以来都是在华外国侨民子女求学“圣地”。1941年,日军强行占领芝罘学校,师生们被分批押往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令人敬佩的是,师生们在绝境中,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教育的坚守、对知识的追求。
自治管理委员会从侨民中筛选有学识者任教师,搭建起覆盖幼儿园至高中的教学体系。虽然办学条件极度简陋,但课程从未中断。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连温饱也解决不了的日子里,老师们仍近乎苛刻地要求学生们规律作息、保持卫生,更以牛津考试标准逐人考核。最终,集中营期间的三届毕业生交出亮眼答卷:前两届全部合格,第三届11名学生有9人达标,多数孩子在战后直接升入了牛津大学。
在孩子们心中,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是最温暖的“飞毛腿叔叔”。这位出生于天津的传教士之子,曾因坚守宗教信仰,拒绝在周日参加100米预赛,改项400米后,不仅夺冠还打破世界纪录。1925年,利迪尔放弃西方的荣誉与优渥生活到中国任教,1942年被押入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
利迪尔在集中营里身兼数职,担任理科教师,组织体育活动,照顾大家起居。为了孩子们的学习成长,他甚至打破“周日不活动”的信仰坚持。然而,1945年2月,这位年仅43岁的“飞毛腿叔叔”,因脑瘤在集中营去世,此时距离日本投降仅剩175天。
【生死相助】 高墙外百姓援手,冒死传递讯息送物资
冬去春来,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深陷绝境。日军切断其与外界所有联系,发霉的杂粮、告罄的药品、隔绝的战报,让这里沦为战争汪洋中的孤舟。营内众人憔悴消瘦、体力枯竭,孩子们的身体发育近乎停滞。危急时刻,侨民们将希望寄托于能出入营地的中国人,一场跨越国界的生命救援悄然拉开序幕。
挑粪工张兴泰是救援的“先行者”。作为少数获准进出的苦力,他冒着生命危险,将侨民的求援信藏在粪桶底层带出营地,辗转交给原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黄乐德四处奔走,最终筹得时值10万美元的善款,经多方协调,以国际红十字会名义采购粮食、药品,分批送入集中营,解了侨民的燃眉之急。
然而,物资只能解燃眉之急,外界的战报才可稳定人心。1944年冬,侨民秘密筹划越狱,24岁的美国教师恒安石(后任美国驻华大使)与英国前海军上尉狄兰被选为执行者。在张兴泰父子、洗衣工杨瑞兰夫妇、木匠刘腾云等人的协助下,二人成功出逃,与潍县抗日游击队会合。在游击队和中国百姓的保护下,他们隐藏在集中营周边,持续向重庆的英美使馆传递营内情况。此后,美军空投的物资经游击队辗转送入营地,战报也随之传入,侨民们知晓战争进展,濒临崩溃的士气得以重振。
中国百姓的援助远不止于此。许多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日军封锁提供物资,有人甚至为此牺牲。潍县西上虞河村青年韩祥,垫木板爬墙送食物时不慎触电身亡,日军竟将其尸体暴尸示众;另有两名村民因试图援助侨民被枪杀,沉闷的枪声成了侨民心中永远的痛。潍县人后代韩崇滨回忆,当年父亲见侨民可怜,凑钱买糖、从家里拿鸡蛋送进集中营,侨民拆铁床作为回应,而父亲压根不知送物资会有“报酬”。
1945年8月17日,美军“鸭子行动”营救小组驾驶轰炸机飞抵潍县上空,解放集中营,中国翻译王成汉随美军空降,侨民重获自由。
中国人民的情谊被侨民们终生铭记。“最艰难时,是潍县人民冒死越过高墙电网,送来食物药品,这是伟大的友谊。”幸存者瓦伦丁·福恩回忆道。2016年,83岁的幸存者戴爱美专程来到中国,向91岁的王成汉转交17封昔日难友的感谢信,含泪说:“中国是我的母亲。”恒安石卸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多次赴潍寻访张兴泰家人,虽因老人离世未能如愿,却始终感念:“张兴泰是我的恩人,我是半个中国人。”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其中有恒安石的贡献,而这一天,正是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解放的纪念日。
如今,潍坊已被授予“国际和平城市”称号,当年的集中营旧址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静静承载着铭记历史、传播和平的使命。旧址旁的和平广场上,“胜利·友谊”雕塑纪念碑肃穆矗立,碑上中英文对照的侨民名单,无声诉说着过往的经历。中国百姓以善良与勇气搭建的援侨通道,早已化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人性光辉的永恒注脚。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的历史,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见证,更是跨越民族与国界的人性赞歌,激励着我们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在历史的回响中不断追寻人类共同的光明未来。